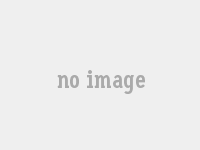
窗含梧桐
在我上班的办公室楼外有五棵法国梧桐。树已经很老了,树身很粗,双手环抱不过来,还是单位建厂那一年栽的。梧桐长得并不周正,东倒西歪的,树干上老树皮东一块西一块。三十多个春秋近两万个日子厚厚地堆积起来,把它
在我上班的办公室楼外有五棵法国梧桐。树已经很老了,树身很粗,双手环抱不过来,还是单位建厂那一年栽的。梧桐长得并不周正,东倒西歪的,树干上老树皮东一块西一块。三十多个春秋近两万个日子厚厚地堆积起来,把它们举得高过楼房。梧桐从接近天穹的高度俯瞰大地,参透一切。秋天里,树叶落了,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,裸身的梧桐并不怕冷,霜打过,雨淋过,雪下过,依然坚定地站在露天里,只有寒风袭来时它的梢头微微哆嗦一下,风前脚走,它后脚就挺直了身子。从厂门口右手边走进来,顺数第四棵梧桐树站立的地方,正是我上班办公的地方。窗含梧桐,门泊梧叶,似乎是很诗意的环境,可我面对梧桐,怎么也诗意不起来。我是看着这棵树一天天长大长高的,梧桐也看着我一天天变老变衰。梧桐亲眼目睹了办公楼的兴衰变化,见证了太多的人事升迁废黜,看着一拨拨人来了,又走了,留下来不走的也就那么几张老面孔,我就是属于这几张老面孔其中之一的。树下有行道,这是一条从厂前门去厕所的必经之道,每天经过的行人不多,如果梧桐能开口说话,也一定能说出走过来的脚步声是属于谁的。如今在梧桐树下来来往往的人除了吃皇粮、拿政府俸禄的厂长是个人物外,其余的不是留守厂子的,就是在厂门口卖小菜摆小摊的引车卖浆者流。树下偶尔停一辆小车,不是厂长的专车就是来厂办事老板的车,难得政府官员的车来厂里了,要来除非厂里出了大事情,除非下岗职工闹事堵马路、集体上访,政府的小车才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厂里,在梧桐树下停了一长串。这些车子锃亮锃亮,小车司机站在车子旁边,一边等头儿开完紧急会议后下楼来,一边用鸡毛掸子轻轻拂掉落在车上的梧树飞絮。快到中午十二点钟的时候,头儿们急匆匆地跑下来,直奔小车,这些车子就鱼贯离开梧桐树,驶出厂门,回到政府大院里去。梧桐树下难得有这么多的贵人来访,来过了,热闹过一阵子,很快就沉寂下来,恢复原有的岑静,车轮碾轧过的树下青苔,那清晰的轮辙印记慢慢地被寂寞填满,被飞絮填满抚平。最喜欢夏天的梧桐,待浪漫的梧絮满世界飘飞游荡过了,赤裸的梧桐梢头便伸出柔嫩的小指头,那说明梧桐开始为自己着装了。没几天时间,小指头变成了小绿扇,整个树身都被树叶遮盖住了,树壮叶肥,冠大阴浓,阳光穿透层层梧叶,返照到窗台上,绿阴阴的,再毒的日头经过梧叶的层层过滤之后就少了火气,多了阴柔,凉咻咻的。微风一动,叶面翻了个身,把阳光赶下去,金泊飘飘闪闪起来。绿叶渗透着阳光,光与影不断地变化着,那叶色就绿得极有层次,比3D画面的晕染效果绚丽一千倍。阳光侵进叶片的边缘,边上的绿色有一抹亮丽的鹅黄。阳光沿着叶脉的纹路往深处走,光的魅力就逐渐减弱,绿色于是就复返本色,凝重起来,浓郁起来。一片梧叶就是一个凉夏的象征么,一片绿色就是一个绿色的希望么?
梧桐也叫悬铃木,春夏之交时分,当最后一轮飞絮落尽的时候,梧桐树上的繁阴里就结出一粒粒毛茸茸的小圆球来。这就是悬铃么?这就是风铃么?微风起处,梧桐就摇响无声的铃铛。心静的时候,我分明听见了梧桐喑哑的铃声,那是心的呼唤。
俗话说,家有梧桐树,引得凤凰来。梧桐为何与珍贵的凤凰联系在一起,这说明梧桐是富贵树种吗?这些,一查互联网就得知,梧桐与凤凰的瓜葛是一个神奇的传说。
有事没事,我总喜欢瞧瞧窗外的梧桐,瞧瞧梧叶在风里有点轻佻地翻动着身子,仿佛那叶子就在我的凝视中一点点地肥大起来,一线线地明亮起来。仿佛分明看见那一丝丝凉气从梧叶上滚过来,扑进窗口,扑到我的怀里。直面如此浓阴罩你的梧桐,直面如此妩媚的她,再硬的心肠也软了,再躁的心情也润了。窗前的梧桐是向窗外北边倾斜,梧叶从树干半人高的地方开始长出来,向着蓝天白云伸展宽大的手掌,时不时沙啦啦地翻起一片无人喝彩的掌声。树干上好像已经风化的树皮卷起来,卷曲成刨花的形状,卷曲成海螺的形状,好似里面藏着岁月的传说,藏着久远的历史。
上了年纪的梧桐啊,你经风历雨,见证过多少人事更迭世事沧桑。不说别的,就在你的周围,就在你面对的正前方的这个办公室的窗口里,就经历了太多的故事。走马灯般的人流,潮水般涌来复退去,这个窗口里发生的事情梧桐树如果能开口的话,它会说出许多来。记不起这五棵梧桐是谁栽的,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那一代创业者们栽下的。那年我们像树苗一样青葱得很。我们刚从学校走出来,第一次坐上汽车,第一次过渡船,第一次来到地区城市,第一次用上自来水,用上香皂。第一次让香喷喷的香皂在赤裸的身子上鼓起了瀑布般的白沫时,感觉周身的泡沫就是可以托起身子的祥云,身轻如羽,飘飘欲飞。我们放下行囊,第一件事就商量晚上去几里路外的火车站看火车的大事情。家乡没有火车,只在电影里看到如长龙般的列车,地区有火车站,看火车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事情。所以迫不及待地吃罢晚饭就兴冲冲地结伴而去看火车。月光下,十几个毛孩子,吵吵嚷嚷地在公路上排成排,一会儿大笑,一会儿奔跑,一会儿唱歌,不觉得就走到了火车站。那时候的火车还是蒸汽机火车头,一个黑古隆冬的大家伙,司炉的年轻人不断地往火炉里添煤,脸上的汗水推洗着煤末,看着他们感觉真新奇,真想帮他铲上几锹煤。那年的办公楼周围是半人的荒草,毒蛇虫豸在草丛里出没,谁也不敢在黑夜里去坪地。刚来厂里就听人说起一位管理员晚上醉酒,去办公楼外撒尿,刚走出楼外,感觉脚下踩着什么软软的东西,吓得他把尿全都撒在裤裆里。第二天早晨去看办公楼外的坪地上横躺着一条死蛇,有一米多长,三个手指头那么粗。管理员幸亏晚上踩着蛇头,把蛇踩死了,要不然的话麻烦就大了。那个时候的工厂没有保洁工,也没有基建民工,要清扫场地,要起房子,全都由工厂组织青工做义务劳动。我们不知搞过多少次义务工。办公楼外的荒草是我们铲除的,场地是我们平整的,连楼外野地周围的树苗也我们亲手栽下的。栽的树挺多,有梧桐、樟树、苦楝树、还有枇杷树,空坪上的四周都栽上了树,而且树与树之间栽得挺密。栽下树苗的那一阵子,经常去浇水,看着树苗活了,绿了,长出碧绿的嫩叶,心里好高兴啊。树苗和我们一般高,树叶尖尖地柔嫩着,心想从此和树苗一块儿生活了,它看着我每天在工厂里来来去去,我也看着它一天天长高
版权声明:本文由zhaosf123传奇新服网原创或收集发布,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相关文章
